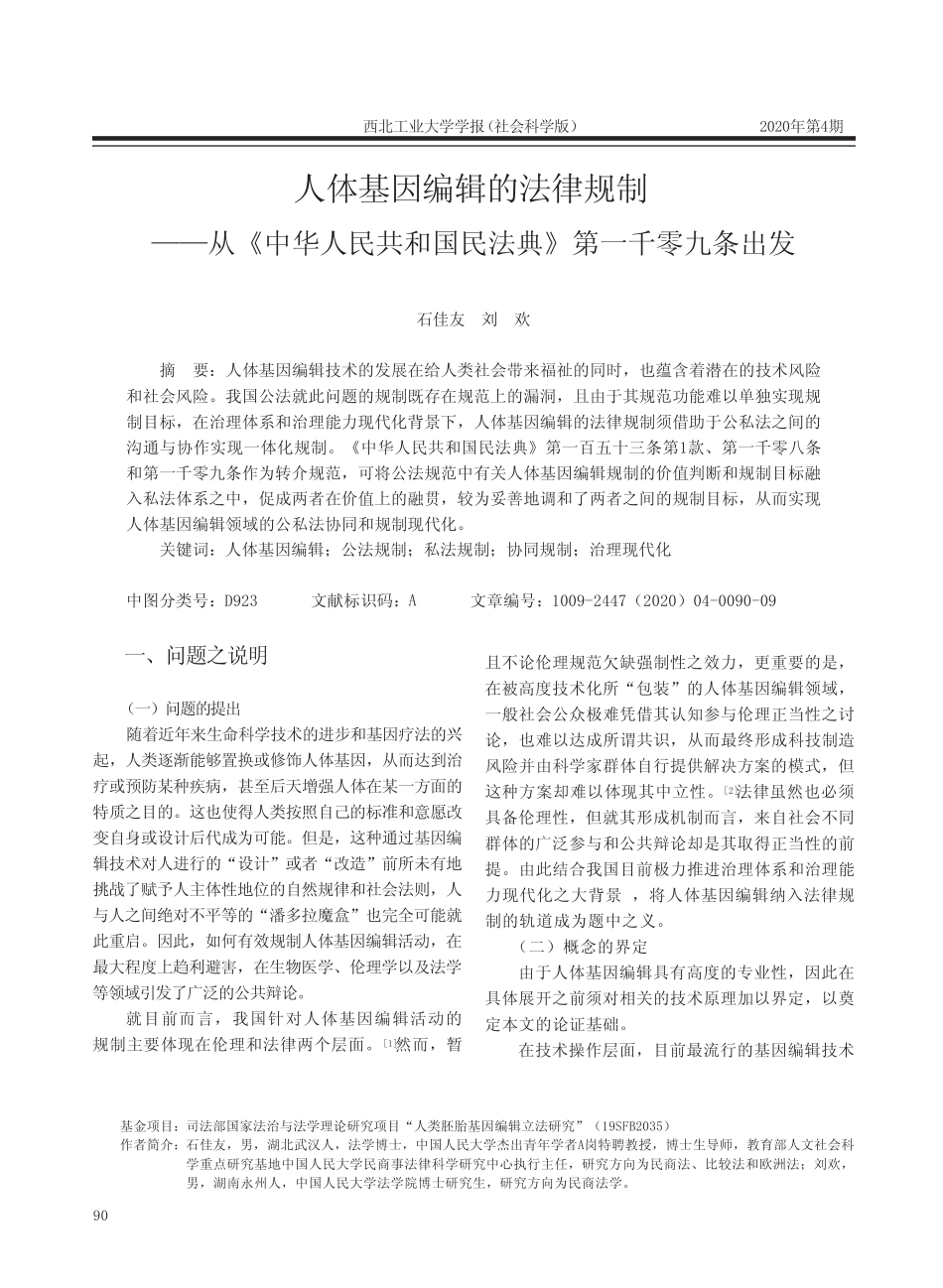902020年第4期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人体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出发石佳友刘欢摘要: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我国公法就此问题的规制既存在规范上的漏洞,且由于其规范功能难以单独实现规制目标,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人体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须借助于公私法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实现一体化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第一千零八条和第一千零九条作为转介规范,可将公法规范中有关人体基因编辑规制的价值判断和规制目标融入私法体系之中,促成两者在价值上的融贯,较为妥善地调和了两者之间的规制目标,从而实现人体基因编辑领域的公私法协同和规制现代化。关键词:人体基因编辑;公法规制;私法规制;协同规制;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4-0090-09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立法研究”(19SFB2035)作者简介:石佳友,男,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A岗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比较法和欧洲法;刘欢,男,湖南永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一、问题之说明(一)问题的提出随着近年来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基因疗法的兴起,人类逐渐能够置换或修饰人体基因,从而达到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甚至后天增强人体在某一方面的特质之目的。这也使得人类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意愿改变自身或设计后代成为可能。但是,这种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人进行的“设计”或者“改造”前所未有地挑战了赋予人主体性地位的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人与人之间绝对不平等的“潘多拉魔盒”也完全可能就此重启。因此,如何有效规制人体基因编辑活动,在最大程度上趋利避害,在生物医学、伦理学以及法学等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公共辩论。就目前而言,我国针对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伦理和法律两个层面。[1]然而,暂且不论伦理规范欠缺强制性之效力,更重要的是,在被高度技术化所“包装”的人体基因编辑领域,一般社会公众极难凭借其认知参与伦理正当性之讨论,也难以达成所谓共识,从而最终形成科技制造风险并由科学家群体自行提供解决方案的模式,但这种方案却难以体现其中立性。[2]法律虽然也必须具备伦理性,但就其形成机制而言,来自社会不同群体的广泛参与和公共辩论却是其取得正当性的前提。由此结合我国目前极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大背景,将人体基因编辑纳入法律规制的轨道成为题中之义。(二)概念的界定由于人体基因编辑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因此在具体展开之前须对相关的技术原理加以界定,以奠定本文的论证基础。在技术操作层面,目前最流行的基因编辑技术91石佳友刘欢:人体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是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系统(ClusteredRegularlyInterspacedShortPalindromicRepeats,CRISPR)。相较于其他技术,CRISPR不仅定位精确,而且操作更为简单,成本更加低廉。可以说,正是CRISPR的产生与发展重新定义了基因编辑,从而使得基因编辑被广泛运用。在具体的人体基因编辑活动中,根据目的之不同,可以分为治疗型基因编辑、预防型基因编辑和增强型基因编辑。[3]其中,治疗和预防型基因编辑通常被认为具备目的正当性;而增强型基因编辑一般被认为不具备正当目的。根据编辑对象之差异,基因编辑还可分为人体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BasicResearch)、体细胞基因编辑(SomaticGenomeEditing)以及生殖细胞基因编辑(HeritableGenomeEditing)。[4]其中,体细胞只对被编辑对象本身产生影响,不具有遗传性;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则会遗传给后代。结合两种分类方式可以发现:其一,人体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只要不孕育出活体生命,风险可控制在实验室之内;其二,针对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即使其出于增强之目的,由于其不利后果仅及于特定主体,故风险可控,但可能打破人与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平等;其三,针对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