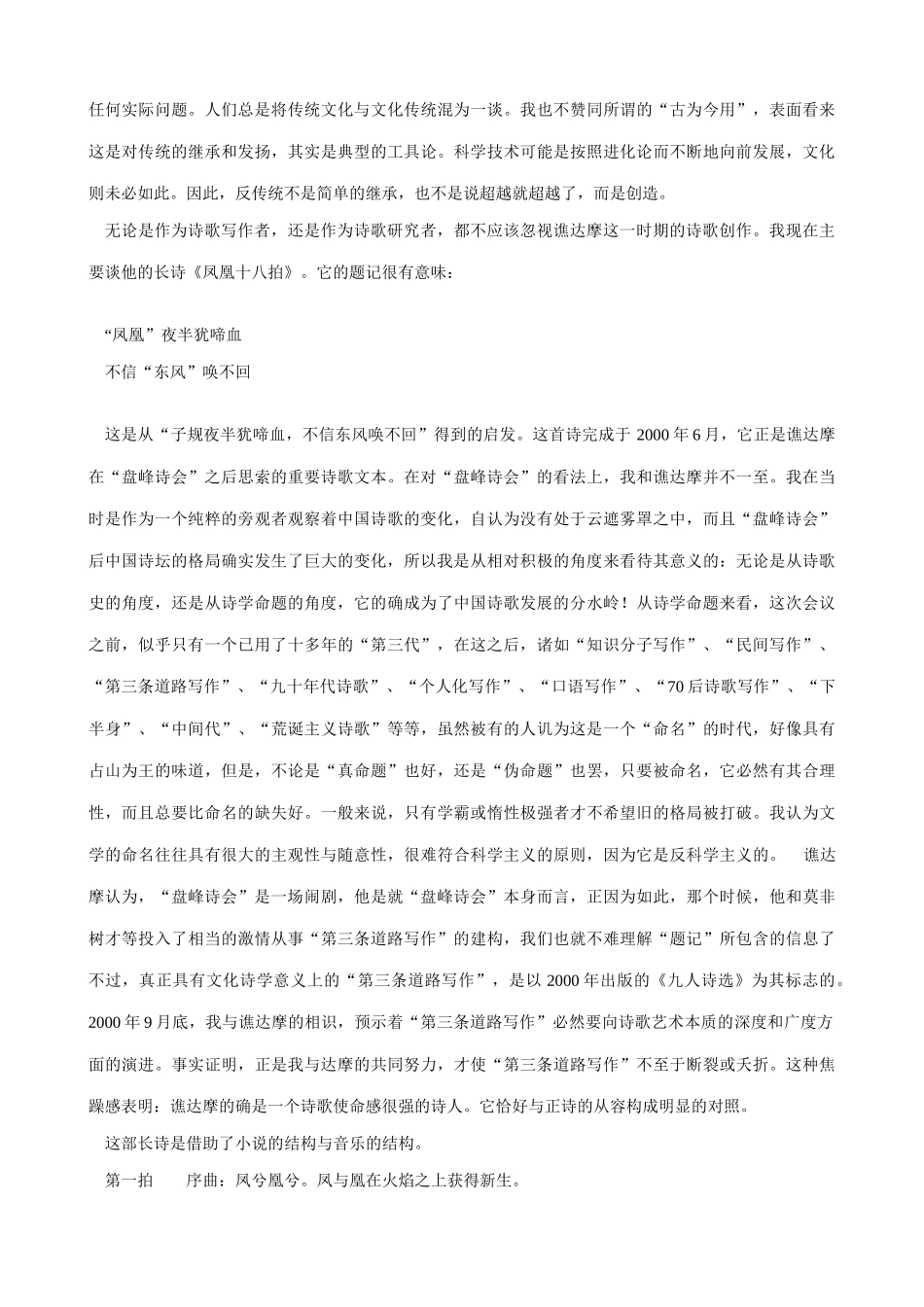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林童中国当代新诗的写作也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则,它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沉闷和无所适从,“盘峰诗会”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不排除“盘峰诗会”期间及之后带有相当多的感情因素和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正是这次论争,使得当下中国诗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由于文学网络的推波助澜,许多诗歌与非诗歌的东西得以彰显出来。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益的,虽然历史并不总是以进化论的方式在前进,但向前看总比向后看更有道理。从事物相异性的角度来考察,也许更能说清一些问题。由于我坚信“批评即选择”,于是我就只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和判断来考察当下中国新诗的面貌。我并非要建立一种批评的标准。在这个写作多元化,阅读多元化,批评多元化,媒介多元化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自然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标准或尺度的质量而言,只有差异的区别,而没有绝对的好坏与是非之分。就当下中国新诗的情况看,虽然提出了众多的诗学命题,而且各自具有相关的文化诗学意义,但如果从影响力和相异性来讲,无疑“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更具有文化诗学范畴比较研究价值。当然,本文并不作总体性的比较,而是从三个各具特点的,并有影响力的诗人着手,分析他们的诗文本,只是切入的角度并不同一。刚好,谯达摩之于“第三条道路写作”,于坚之于“民间写作”,王家新之于“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谯达摩批判:凤凰的虚无与永恒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谯达摩以他独有的诗歌方式引人注目。从年龄来看,出生于1966年的谯达摩与于坚、王家新并不属于同龄人。按照目前流行的诗歌史的划分观点,于坚、王家新在“第三代”,谯达摩在“中间代”,似乎比较研究的基点不好确定,但由于有了“盘峰诗会”,诗人年龄的差别根本就不构成任何问题。谯达摩的诗歌写作,并不存在对事物重新命名的焦虑,而且也不会对他的创造性构成负面影响,相反他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处理得相当从容。这得益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滋养。我现在理解的反传统,并非将传统从我们的意识与思维中驱逐出去,更不可能从我们的血液中加以彻底的清理,甚至于也无法真正区分出哪是精华哪是糟粕,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人们总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混为一谈。我也不赞同所谓的“古为今用”,表面看来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实是典型的工具论。科学技术可能是按照进化论而不断地向前发展,文化则未必如此。因此,反传统不是简单的继承,也不是说超越就超越了,而是创造。无论是作为诗歌写作者,还是作为诗歌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谯达摩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我现在主要谈他的长诗《凤凰十八拍》。它的题记很有意味:“凤凰”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是从“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得到的启发。这首诗完成于2000年6月,它正是谯达摩在“盘峰诗会”之后思索的重要诗歌文本。在对“盘峰诗会”的看法上,我和谯达摩并不一至。我在当时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观察着中国诗歌的变化,自认为没有处于云遮雾罩之中,而且“盘峰诗会”后中国诗坛的格局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是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其意义的:无论是从诗歌史的角度,还是从诗学命题的角度,它的确成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分水岭!从诗学命题来看,这次会议之前,似乎只有一个已用了十多年的“第三代”,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虽然被有的人讥为这是一个“命名”的时代,好像具有占山为王的味道,但是,不论是“真命题”也好,还是“伪命题”也罢,只要被命名,它必然有其合理性,而且总要比命名的缺失好。一般来说,只有学霸或惰性极强者才不希望旧的格局被打破。我认为文学的命名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很难符合科学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反科学主义的。谯达摩认为,“盘峰诗会”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