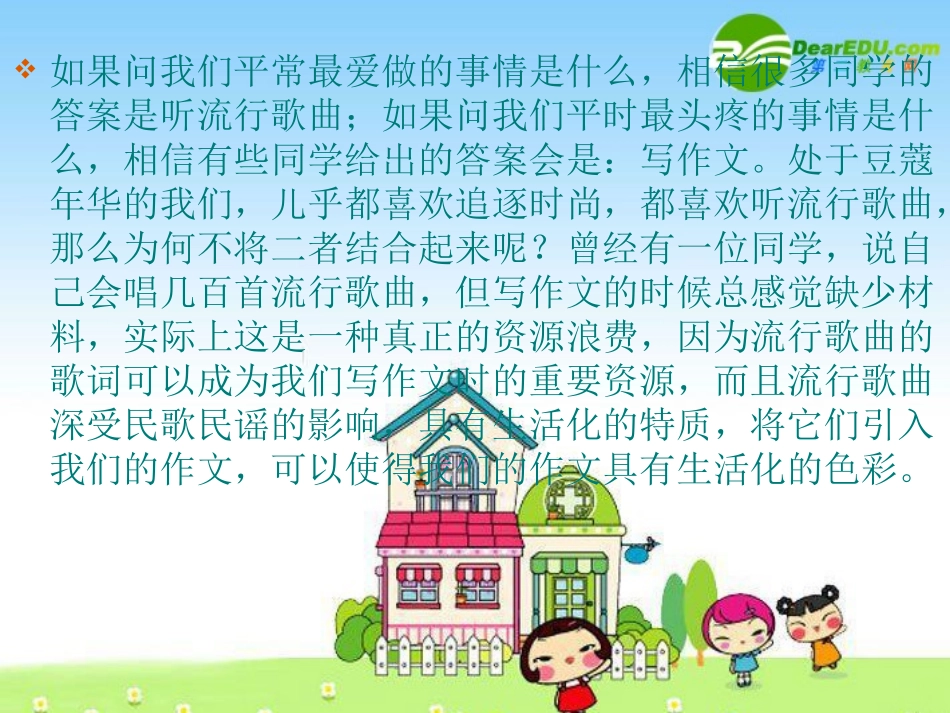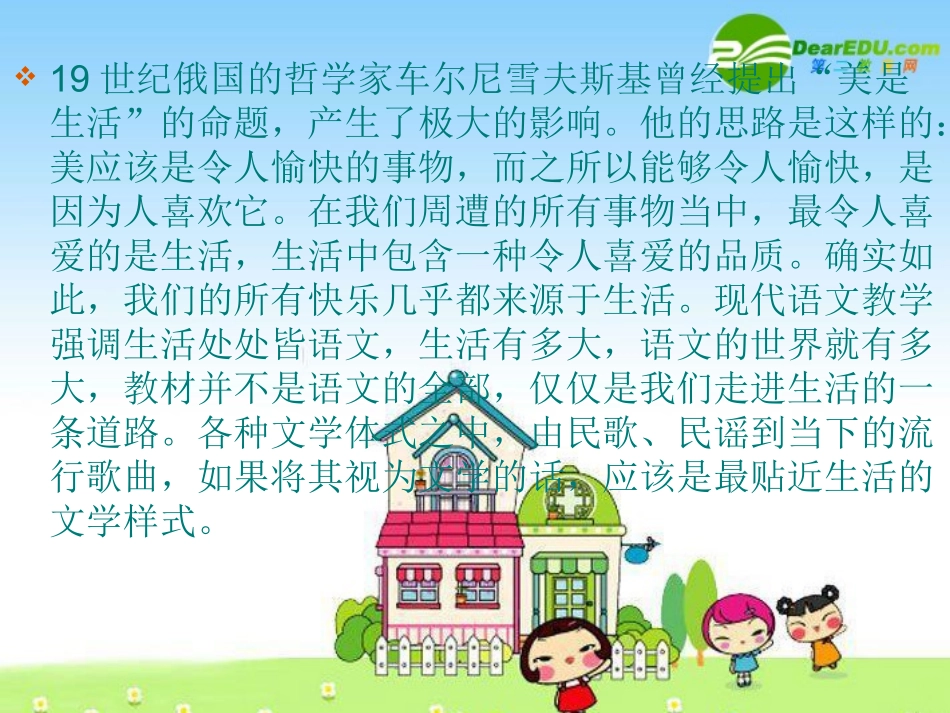如果问我们平常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相信很多同学的答案是听流行歌曲;如果问我们平时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相信有些同学给出的答案会是:写作文。处于豆蔻年华的我们,儿乎都喜欢追逐时尚,都喜欢听流行歌曲,那么为何不将二者结合起来呢?曾经有一位同学,说自己会唱几百首流行歌曲,但写作文的时候总感觉缺少材料,实际上这是一种真正的资源浪费,因为流行歌曲的歌词可以成为我们写作文时的重要资源,而且流行歌曲深受民歌民谣的影响,具有生活化的特质,将它们引入我们的作文,可以使得我们的作文具有生活化的色彩。19世纪俄国的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思路是这样的: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事物,而之所以能够令人愉快,是因为人喜欢它。在我们周遭的所有事物当中,最令人喜爱的是生活,生活中包含一种令人喜爱的品质。确实如此,我们的所有快乐几乎都来源于生活。现代语文教学强调生活处处皆语文,生活有多大,语文的世界就有多大,教材并不是语文的全部,仅仅是我们走进生活的一条道路。各种文学体式之中,由民歌、民谣到当下的流行歌曲,如果将其视为文学的话,应该是最贴近生活的文学样式。流行歌曲首先要具有流行的因素,从“流行”范围的角度来说,显然应该是广大的民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根阶层”,这就要求歌词写作要具有民间性,对于这一特质,如果进行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传统的民歌和民谣的写作策略。民歌和民谣可以说是民族文学的源头,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都是具有民间性的文学,随后的文人写作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从民歌和民谣中汲取营养。所以我们可以说民歌和民谣的民间性以及文人写作的技巧性是影响当代流行歌曲歌词写作的两个维度,这一点,黄霑和方文山的歌词写作比较有代表性。这里,我们首先从民歌民谣说起。民歌与民谣歌与谣最早的分称可以追根溯源到《诗经·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们的不同主要有两种解释:“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诗故训传》);“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韩诗章曲》)。具体来讲,谣并不像歌那样以旋律为主,再填上相应的歌词,注重演唱本身表现力的一种艺术形式。旋律在谣中往往退而求其次,曲调不固定,即便有也不求丰富多彩,以吟咏的方式见常,章句格式也比较自由,节奏上一般比较紧促。正是因为谣中旋律的地位有所降低,彼消此涨,谣中的歌词跃然成为了重头表现的部分。以前很多的民谣多为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即兴而发,歌词或许比较乡野而少文质。然而自从民谣的创作风格被文人吸纳之后,他们在继承了民谣固有的通俗平易、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的同时,以自身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了民谣的思想文化内涵,民谣的批判性被保留了下来甚至有所加强。实际上,民歌和民谣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写作文主要借鉴的民歌和民谣的歌词来说,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歌谣》中讲:“本来歌谣都是原始的诗。以‘辞’而论,并无分别;只因一个合乐,一个徒歌,以‘声’而论,便自不同了。”也就是说,民歌是入乐的,民谣虽然也可以入乐,但是限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并不借助于音乐来传播,发展到了现代形态,这可能是民谣的讽刺性得以强化的根本原因。这里不进行详细的阐释。民歌,人民之歌。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每一时代、地域、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种供人们自娱自乐的歌曲。它们会以不同的形式传递民族的历史、文明以及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文学史的发展实际表明,民歌是各个民族的文学的最早的体式形态。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风”,原因在于这部分的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他们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我们有理由说,我们的祖先要比我们这些后来者更开朗和开放,这倒不是表现在他们有网恋之类的行为,而是他们大多开口就能唱出美丽的歌谣。《诗经》中的《风》,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当年在田间地头劳动时随口唱出来的。就是这些随口唱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