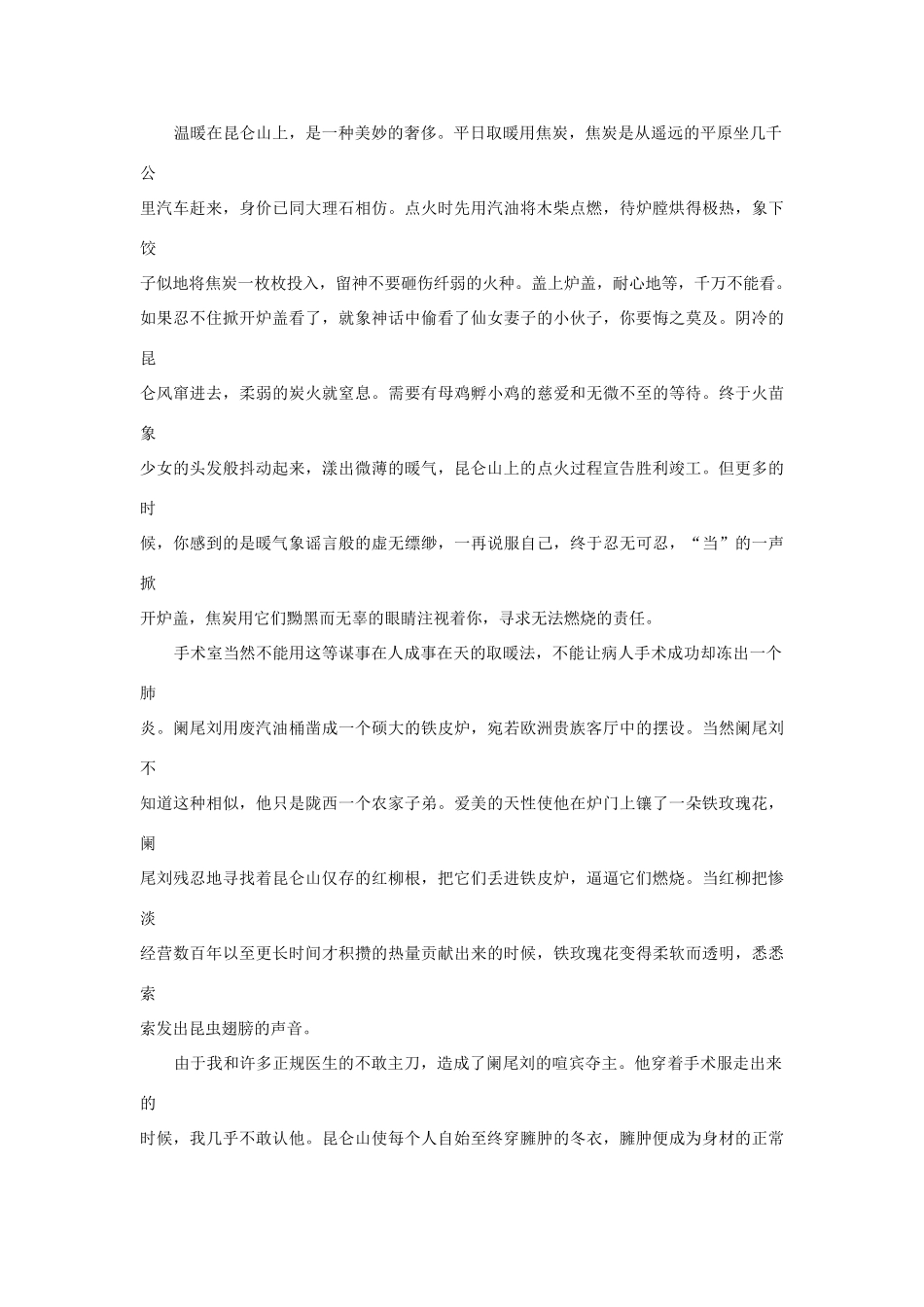阑尾刘作者:毕淑敏 “我切过的阑尾,能够装满一马车。”刘坐在昆仑山一块钢蓝色的石头上,对我说。 我从内地军医大学毕业,又在农场锻炼两载,刚分到昆仑山上。听过许多医学教授讲课,开肠破肚的手术也见过不少,从未见过谁如此大言不惭地谈论人身上这个多余的器官。 昆仑山缺氧。缺氧的感觉类乎酒醉,醺醺然,飘飘欲仙。这时候讲的话。大约不可信。 我看着刘。他面如焦枣。焦枣是完全不够用的,更要憔悴黑紫许多,脸皮不但有横行而且有纵行的皱纹,仿佛井田制。昆仑山是大手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人都雕刻成这个样子。 看在昆仑山的份上,我尊重了他。昆仑山有特殊的风俗,不在于你年龄大小,资历高低,而在于你呆在山上时间的长短。你要在昆仑山生活下去,必须要同山有默契。 后来我听人叫他阑尾刘,好象天津的泥人张或是北京的白水羊头李。我想昆仑山上真是没见过世面,但嘴上也得这样叫。 第一次同阑尾刘一道做手术,是在冬天。昆仑山本没有四季可分,只有一个永恒的节气就是大寒。我之所以特别记住了那个日子,是因为手术室里陌生的温暖。 我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手术室。平房、土地,没有无影灯。手指在普通灯光下显出丝绒般的阴影,手术时的感觉象在演盲人摸象。 “这怎么能做手术?又不是打地道战!”我惊呼,严格的医学教育使我本能地拒绝执刀。 “这怎么不能做手术?打起仗来,比这还不如呢!”阑尾刘不屑地说。 天天叫备战,昆仑山离两霸虽远,原子弹一甩起来可没遮拦。 红柳根在汽油桶改制的大铁皮炉里,汹涌澎湃地燃烧,裸露肌肤的病人居然有了汗意。 我拒绝做手术。如果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你可怎么办?我始终认为“下不了台”这句话,不是为演员或是领导干部预备的话,而是一位失败的医生的惨痛教训。 “我来。”阑尾刘说。 他并不是医生,只是手术室的卫生员,负责配合手术和室内的清洁与取暖。 温暖在昆仑山上,是一种美妙的奢侈。平日取暖用焦炭,焦炭是从遥远的平原坐几千公里汽车赶来,身价已同大理石相仿。点火时先用汽油将木柴点燃,待炉膛烘得极热,象下饺子似地将焦炭一枚枚投入,留神不要砸伤纤弱的火种。盖上炉盖,耐心地等,千万不能看。如果忍不住掀开炉盖看了,就象神话中偷看了仙女妻子的小伙子,你要悔之莫及。阴冷的昆仑风窜进去,柔弱的炭火就窒息。需要有母鸡孵小鸡的慈爱和无微不至的等待。终于火苗象少女的头发般抖动起来,漾出微薄的暖气,昆仑山上的点火过程宣告胜利竣工。但更多的时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