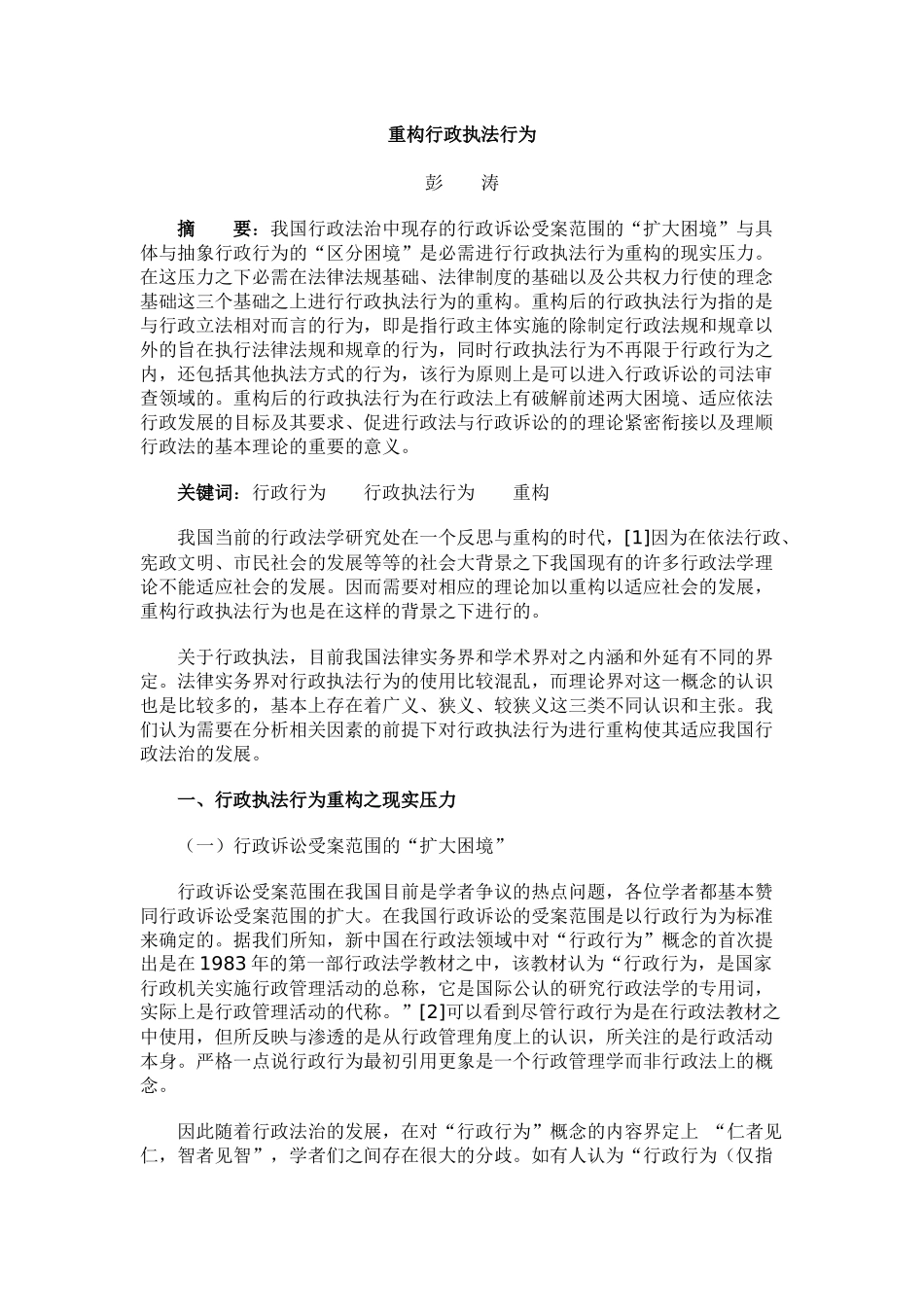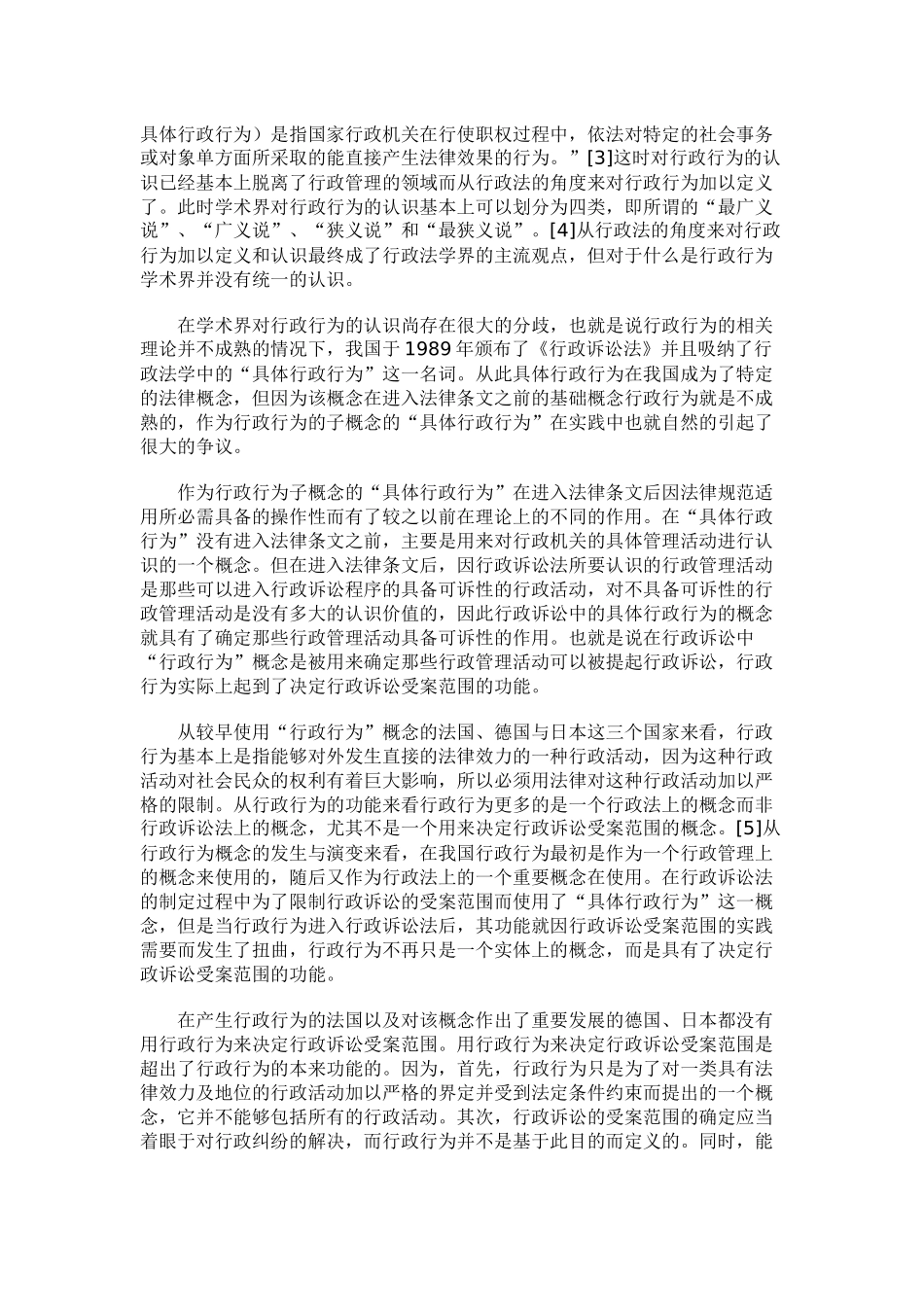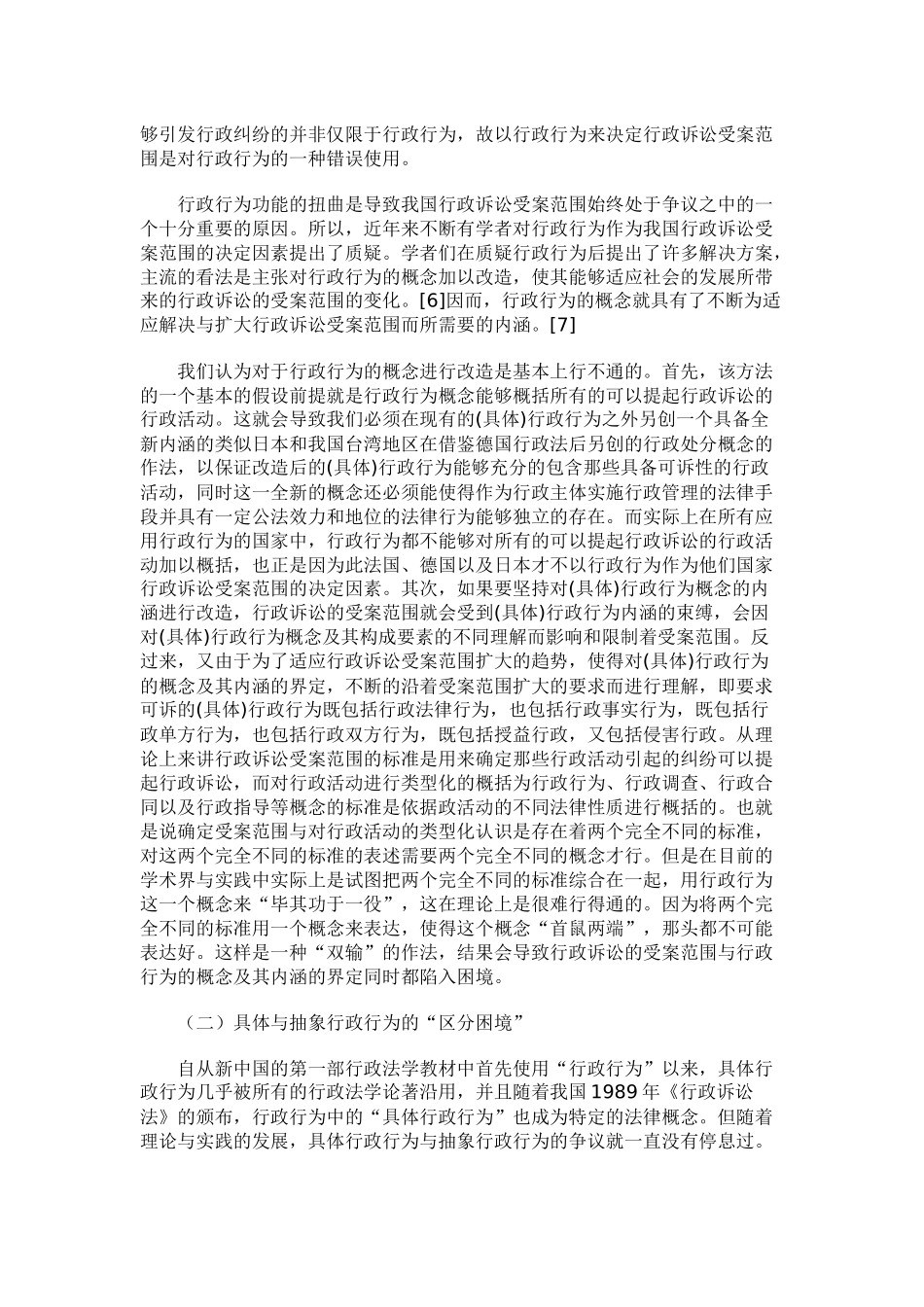重构行政执法行为彭涛摘要:我国行政法治中现存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困境”与具体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困境”是必需进行行政执法行为重构的现实压力。在这压力之下必需在法律法规基础、法律制度的基础以及公共权力行使的理念基础这三个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执法行为的重构。重构后的行政执法行为指的是与行政立法相对而言的行为,即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旨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同时行政执法行为不再限于行政行为之内,还包括其他执法方式的行为,该行为原则上是可以进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领域的。重构后的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法上有破解前述两大困境、适应依法行政发展的目标及其要求、促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的理论紧密衔接以及理顺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的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行政行为行政执法行为重构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处在一个反思与重构的时代,[1]因为在依法行政、宪政文明、市民社会的发展等等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我国现有的许多行政法学理论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而需要对相应的理论加以重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重构行政执法行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关于行政执法,目前我国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之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界定。法律实务界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使用比较混乱,而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存在着广义、狭义、较狭义这三类不同认识和主张。我们认为需要在分析相关因素的前提下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重构使其适应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一、行政执法行为重构之现实压力(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困境”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我国目前是学者争议的热点问题,各位学者都基本赞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以行政行为为标准来确定的。据我们所知,新中国在行政法领域中对“行政行为”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83年的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之中,该教材认为“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总称,它是国际公认的研究行政法学的专用词,实际上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代称。”[2]可以看到尽管行政行为是在行政法教材之中使用,但所反映与渗透的是从行政管理角度上的认识,所关注的是行政活动本身。严格一点说行政行为最初引用更象是一个行政管理学而非行政法上的概念。因此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在对“行政行为”概念的内容界定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有人认为“行政行为(仅指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依法对特定的社会事务或对象单方面所采取的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3]这时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已经基本上脱离了行政管理的领域而从行政法的角度来对行政行为加以定义了。此时学术界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类,即所谓的“最广义说”、“广义说”、“狭义说”和“最狭义说”。[4]从行政法的角度来对行政行为加以定义和认识最终成了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对于什么是行政行为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学术界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尚存在很大的分歧,也就是说行政行为的相关理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国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并且吸纳了行政法学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名词。从此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成为了特定的法律概念,但因为该概念在进入法律条文之前的基础概念行政行为就是不成熟的,作为行政行为的子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也就自然的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作为行政行为子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进入法律条文后因法律规范适用所必需具备的操作性而有了较之以前在理论上的不同的作用。在“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进入法律条文之前,主要是用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管理活动进行认识的一个概念。但在进入法律条文后,因行政诉讼法所要认识的行政管理活动是那些可以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具备可诉性的行政活动,对不具备可诉性的行政管理活动是没有多大的认识价值的,因此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就具有了确定那些行政管理活动具备可诉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概念是被用来确定那些行政管理活动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实际上起到了决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从较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