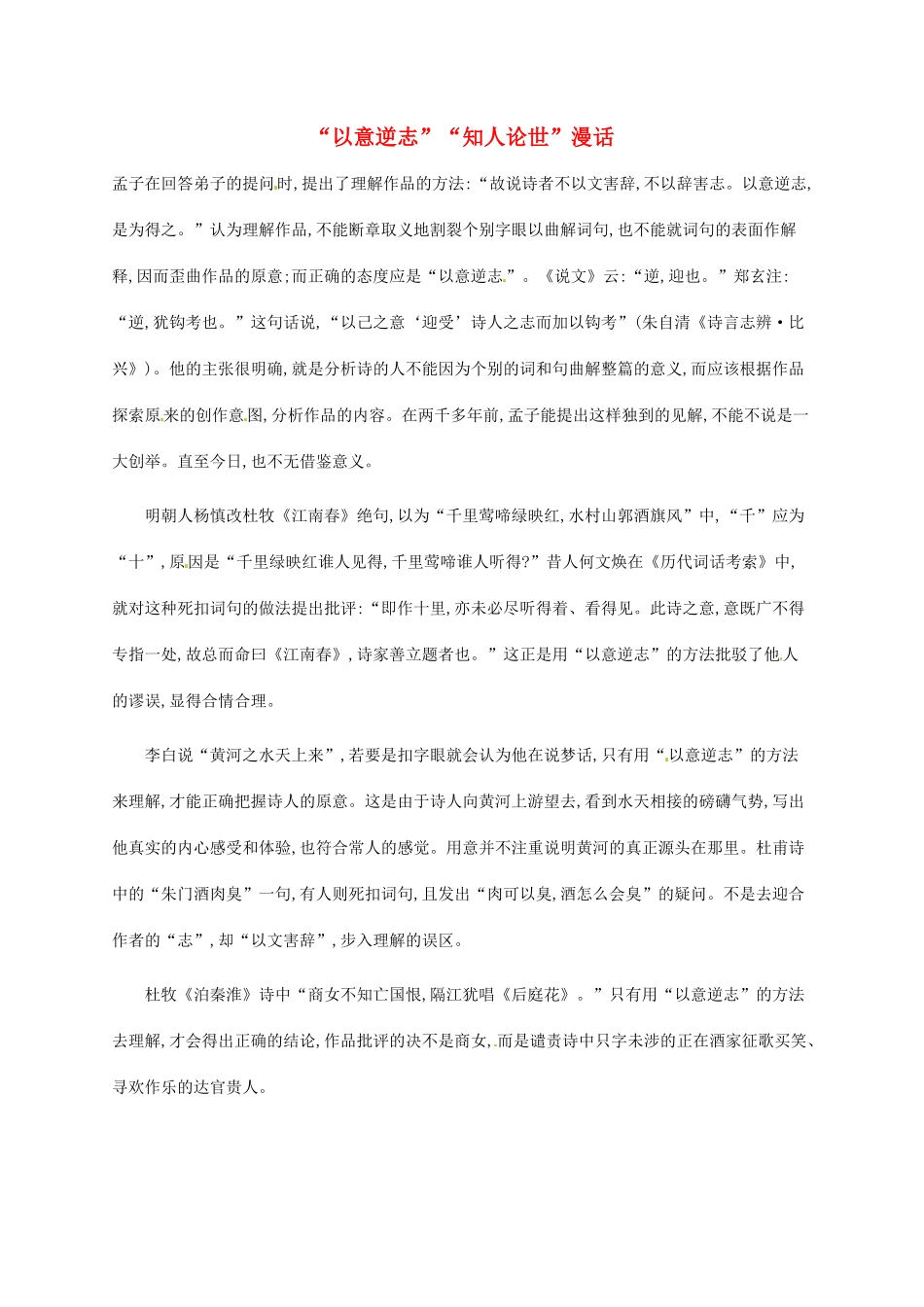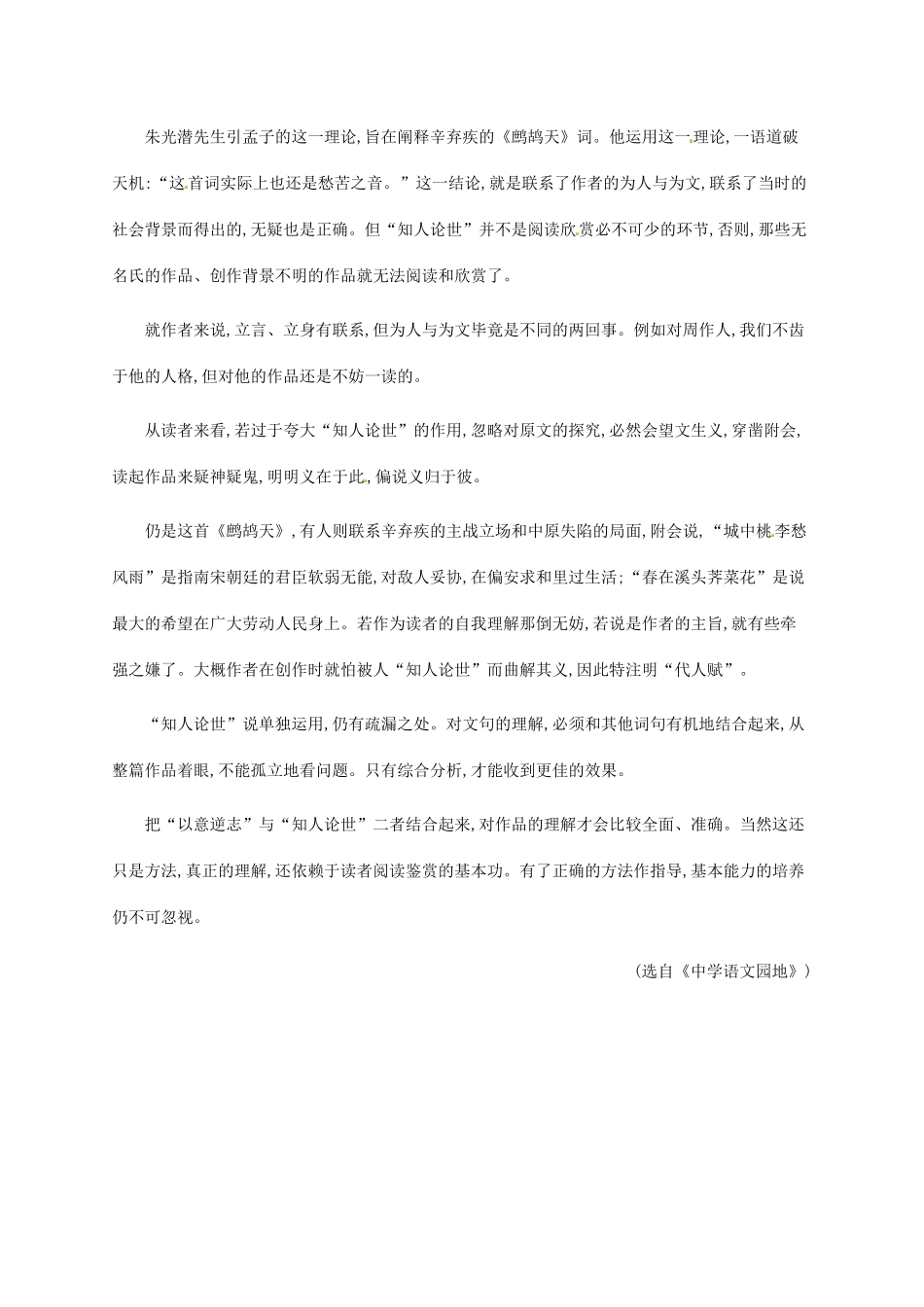“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漫话孟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提出了理解作品的方法:“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认为理解作品,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个别字眼以曲解词句,也不能就词句的表面作解释,因而歪曲作品的原意;而正确的态度应是“以意逆志”。《说文》云:“逆,迎也。”郑玄注:“逆,犹钩考也。”这句话说,“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他的主张很明确,就是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词和句曲解整篇的意义,而应该根据作品探索原来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的内容。在两千多年前,孟子能提出这样独到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一大创举。直至今日,也不无借鉴意义。明朝人杨慎改杜牧《江南春》绝句,以为“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中,“千”应为“十”,原因是“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千里莺啼谁人听得?”昔人何文焕在《历代词话考索》中,就对这种死扣词句的做法提出批评:“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这正是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批驳了他人的谬误,显得合情合理。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若要是扣字眼就会认为他在说梦话,只有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诗人的原意。这是由于诗人向黄河上游望去,看到水天相接的磅礴气势,写出他真实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也符合常人的感觉。用意并不注重说明黄河的真正源头在那里。杜甫诗中的“朱门酒肉臭”一句,有人则死扣词句,且发出“肉可以臭,酒怎么会臭”的疑问。不是去迎合作者的“志”,却“以文害辞”,步入理解的误区。杜牧《泊秦淮》诗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只有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去理解,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品批评的决不是商女,而是谴责诗中只字未涉的正在酒家征歌买笑、寻欢作乐的达官贵人。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能正确地理解作品,鉴赏作品,而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正是指导我们正确理解作品的至理名言。孟子进而提出了“知人论世”的主张,作为“以意逆志”的补充。也就是要结合作者的思想和时代背景理解作品。王国维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可解者寡矣。”这为我们正确地理解作品,指出了一条途径。然而“以意逆志”,是用什么样的“意”,去迎什么样的“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具体的方法离不开世界观的制约,他总要受的一定的指导思想的支配并服务于这一指导思想。孟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