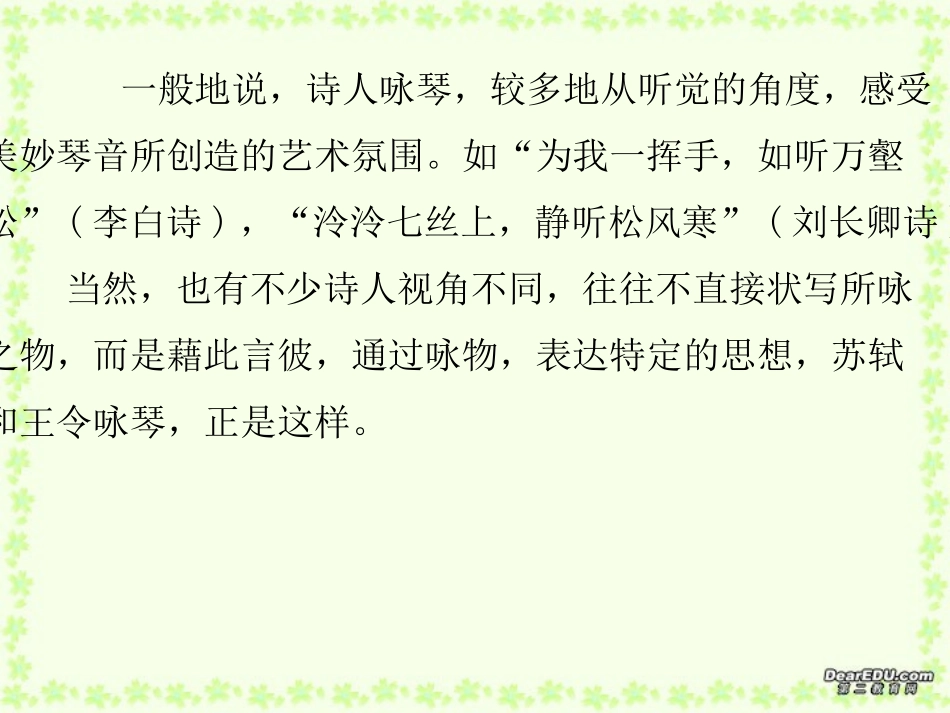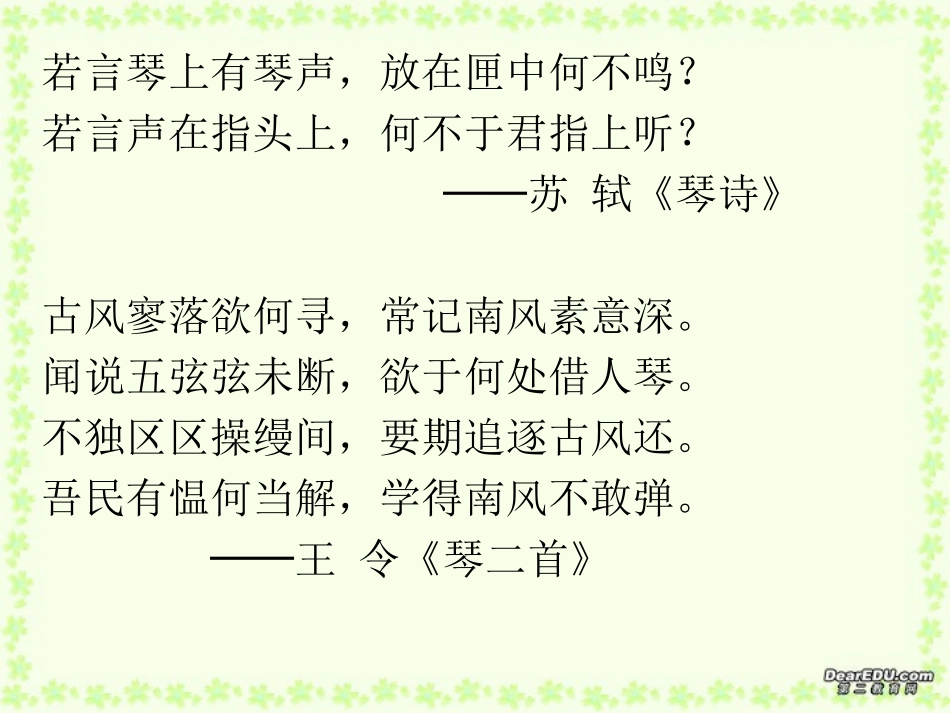诗歌比较鉴赏能力训练1一般地说,诗人咏琴,较多地从听觉的角度,感受美妙琴音所创造的艺术氛围。如“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李白诗),“泠泠七丝上,静听松风寒”(刘长卿诗),当然,也有不少诗人视角不同,往往不直接状写所咏之物,而是藉此言彼,通过咏物,表达特定的思想,苏轼和王令咏琴,正是这样。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琴诗》古风寥落欲何寻,常记南风素意深。闻说五弦弦未断,欲于何处借人琴。不独区区操缦间,要期追逐古风还。吾民有愠何当解,学得南风不敢弹。──王令《琴二首》这二首咏琴诗,打上了宋诗的烙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议论入诗。宋代诗坛,注重议论入诗,借诗阐发一些哲理;二是注重针砭现实,三是语言力避艰深晦涩,而求明白晓畅。苏诗刻意表现理趣,王诗体现曲讽,苏轼的《琴诗》,内容和形式都很特殊。在内容上,该诗借物言理,言近意远;在形式上,该诗采用只问不答、只驳不辩、答辩自在其中的手法。《琴二首》与苏轼《琴诗》比,虽内容和形式上不求创新,但借琴抒怀表意,也很耐人寻味。“区区”是喜悦自得的样子,“操缦”是拨弄琴弦,即弹琴,“愠”是怨恨、忧怨的意思。诗人是把矛头直指当权者,抨击其不顾百姓的倒行逆施。名为咏琴,实为讽刺现实。李端《鸣筝》、柳中庸《听筝》与白居易《夜筝》比较谈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李端《鸣筝》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更入几重离别恨,江南歧路洛阳城。——柳中庸《听筝》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白居易《夜筝》李端的《鸣筝》,其着眼点在于摹写弹筝者的神态。此诗虽仅四句二十字,却极其自然地将地点、人物、事件等交代了出来。其格调是轻快的,这与柳中庸的《听筝》不同之处。柳中庸的《听筝》,则从听筝者的角度着墨,重在抒写听筝感受。全诗直接写弹筝者动作的仅四字。“听秦筝”三字,点破题旨。“无限秦人悲怨声”,为全诗定下了“悲怨”的抒情基调,诗人借助了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抒写听筝的感受。最后两句,将诗人的离情别恨与“悲怨”的筝声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映衬。写筝声,未用一个象声词,但借助于比喻、联想等法,将筝乐化为具体可感之物,也将诗人的离情别恨抒写得淋漓尽致。白居易的《夜筝》,此诗虽说也抒写了听筝者的情感,但并非李端《鸣筝》中那妙龄女子的爱情,而是“别有深情”;虽说也写出了听筝者的感受,但这与柳中庸的《听筝》给人的感受相异,写法上也不像柳诗那样采用巧比妙喻等多种手法,而主要是采用了乐曲中的“休止”,国画中的‘空白”技法。这首《夜筝》则主要通过“弦凝”、“指咽”与“声停”等特写镜头,以“无声”表达深情。这三首同题材的诗,都写听筝,但其着眼点都不在表现弹筝者精湛的技艺,也不在描绘筝乐的内容,而是“听筝之意不在筝”,借听筝以写人,三首诗各有侧重。李端的诗,着重摹写弹筝者的神态;柳中庸的诗,着重描写诗人听筝的感受,并以此抒写自己的离情别恨;白居易的诗,则主要表现诗中主人公“别有深情一万重”。在写法上,李端的诗,主要用典,以一个生动的细节表情达意,具有诗趣;柳中庸的诗,主要采用新颖贴切的比喻,将表达筝之“悲怨声”与诗人之“离别恨”结合起来,化无形为有形;白居易的诗,则主要运用“空白”的技法,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