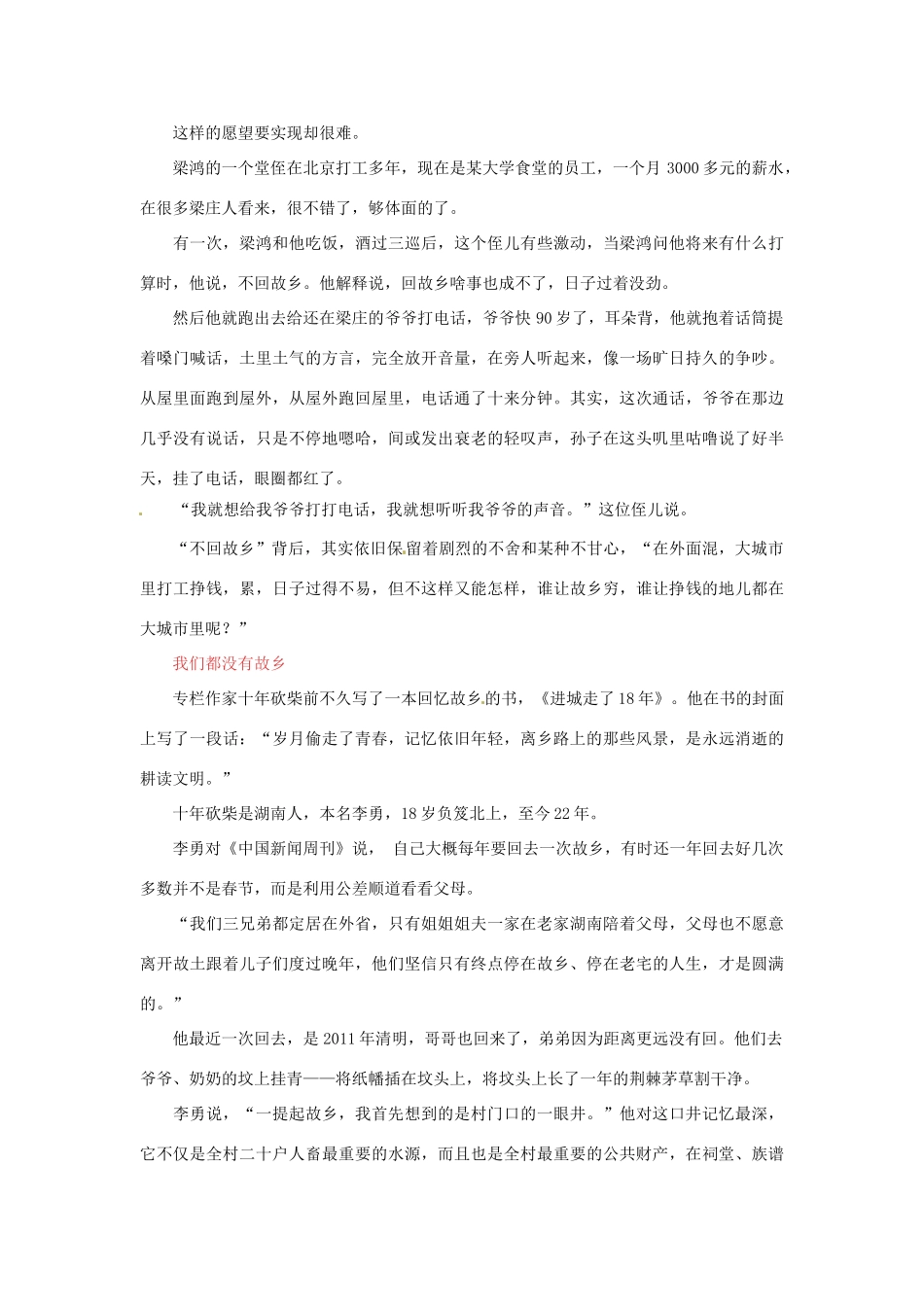回不回家过年作者:刘炎迅 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 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 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 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乡关不再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 2008 年和2009 年,用近 5 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 20 多年。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 3000 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 90 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