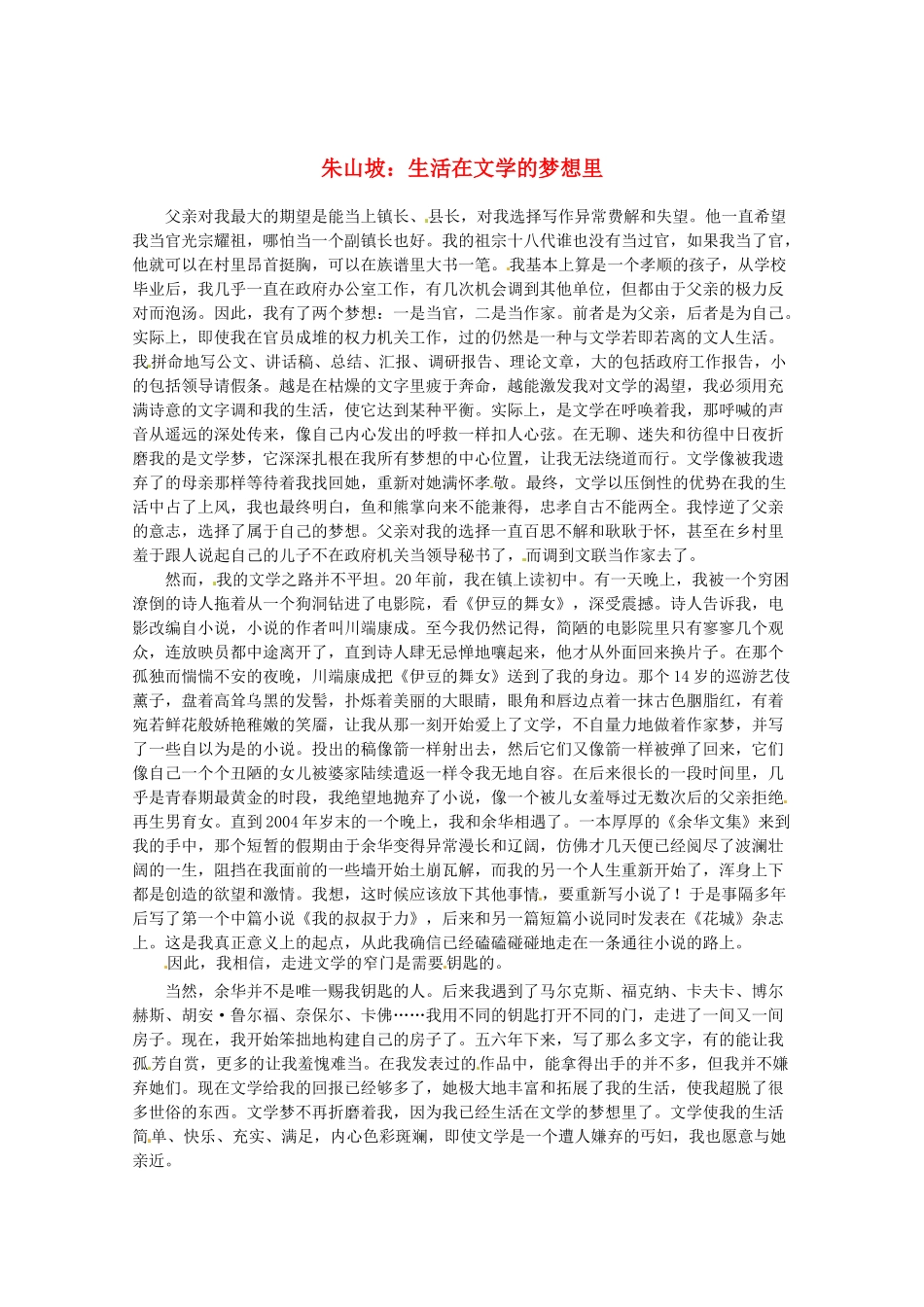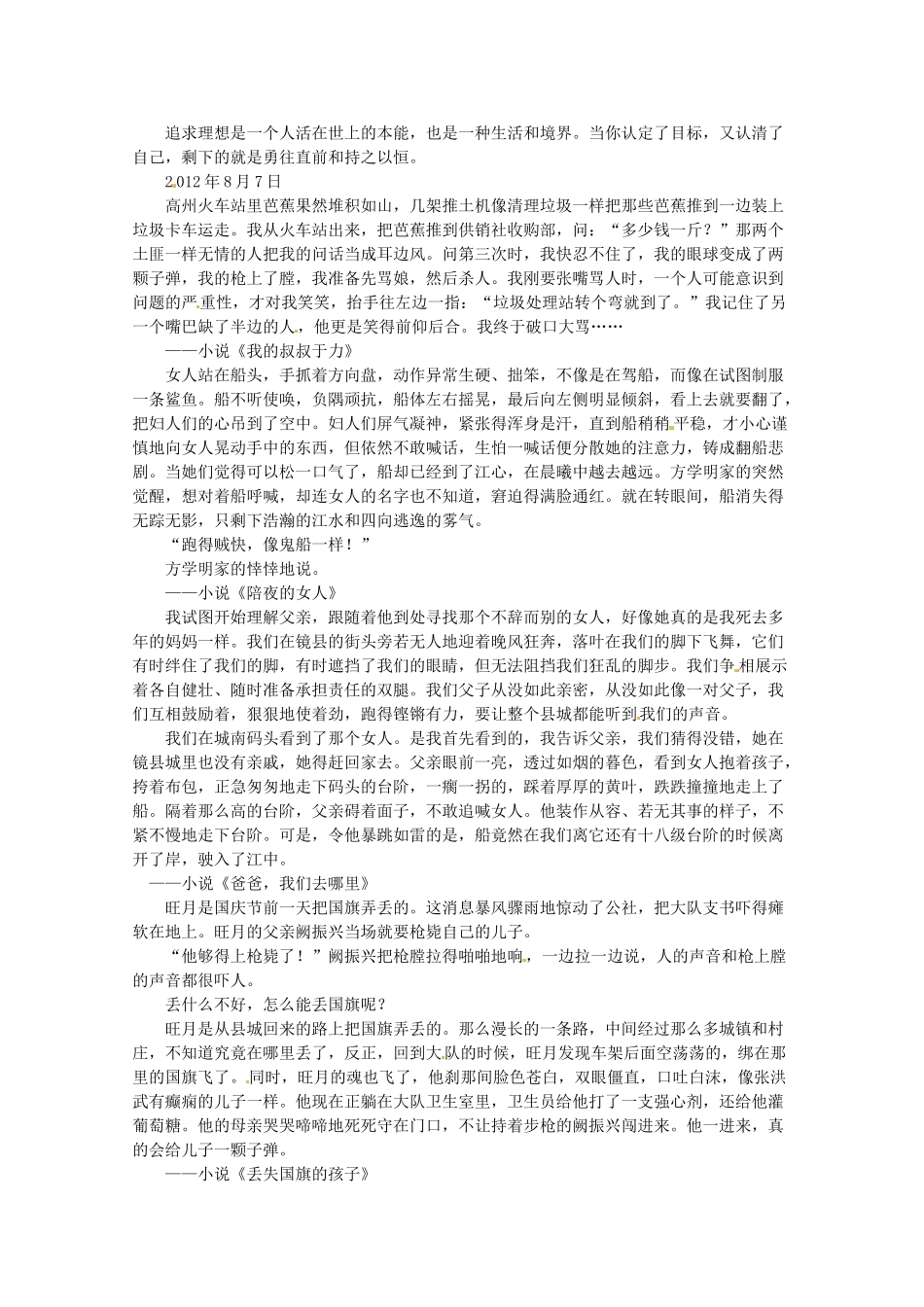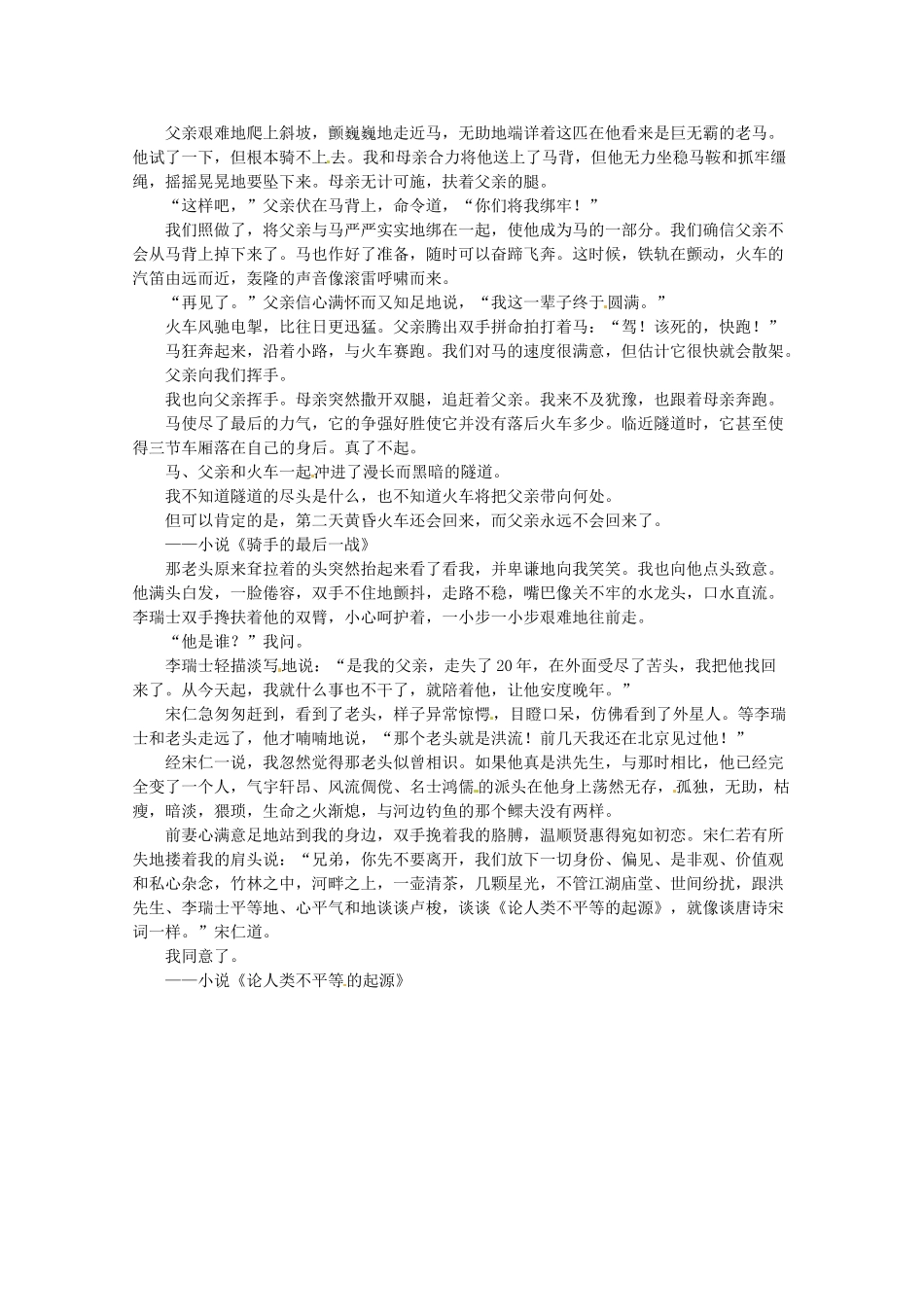朱山坡:生活在文学的梦想里 父亲对我最大的期望是能当上镇长、县长,对我选择写作异常费解和失望。他一直希望我当官光宗耀祖,哪怕当一个副镇长也好。我的祖宗十八代谁也没有当过官,如果我当了官,他就可以在村里昂首挺胸,可以在族谱里大书一笔。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从学校毕业后,我几乎一直在政府办公室工作,有几次机会调到其他单位,但都由于父亲的极力反对而泡汤。因此,我有了两个梦想:一是当官,二是当作家。前者是为父亲,后者是为自己。实际上,即使我在官员成堆的权力机关工作,过的仍然是一种与文学若即若离的文人生活。我拼命地写公文、讲话稿、总结、汇报、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大的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小的包括领导请假条。越是在枯燥的文字里疲于奔命,越能激发我对文学的渴望,我必须用充满诗意的文字调和我的生活,使它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是文学在呼唤着我,那呼喊的声音从遥远的深处传来,像自己内心发出的呼救一样扣人心弦。在无聊、迷失和彷徨中日夜折磨我的是文学梦,它深深扎根在我所有梦想的中心位置,让我无法绕道而行。文学像被我遗弃了的母亲那样等待着我找回她,重新对她满怀孝敬。最终,文学以压倒性的优势在我的生活中占了上风,我也最终明白,鱼和熊掌向来不能兼得,忠孝自古不能两全。我悖逆了父亲的意志,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梦想。父亲对我的选择一直百思不解和耿耿于怀,甚至在乡村里羞于跟人说起自己的儿子不在政府机关当领导秘书了,而调到文联当作家去了。 然而,我的文学之路并不平坦。20 年前,我在镇上读初中。有一天晚上,我被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拖着从一个狗洞钻进了电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深受震撼。诗人告诉我,电影改编自小说,小说的作者叫川端康成。至今我仍然记得,简陋的电影院里只有寥寥几个观众,连放映员都中途离开了,直到诗人肆无忌惮地嚷起来,他才从外面回来换片子。在那个孤独而惴惴不安的夜晚,川端康成把《伊豆的舞女》送到了我的身边。那个 14 岁的巡游艺伎薰子,盘着高耸乌黑的发髻,扑烁着美丽的大眼睛,眼角和唇边点着一抹古色胭脂红,有着宛若鲜花般娇艳稚嫩的笑靥,让我从那一刻开始爱上了文学,不自量力地做着作家梦,并写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小说。投出的稿像箭一样射出去,然后它们又像箭一样被弹了回来,它们像自己一个个丑陋的女儿被婆家陆续遣返一样令我无地自容。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青春期最黄金的时段,我绝望地抛弃了小说,像一个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