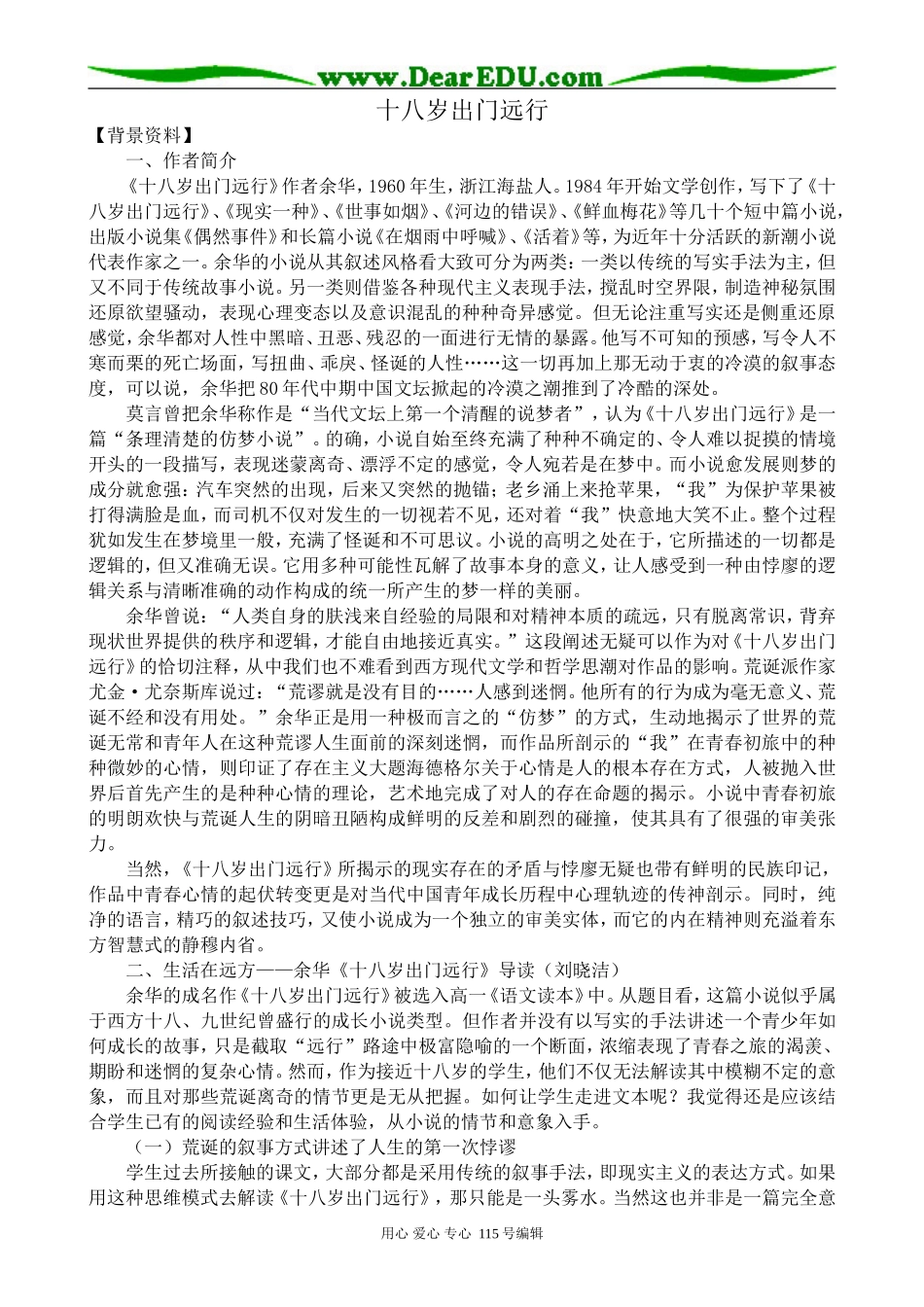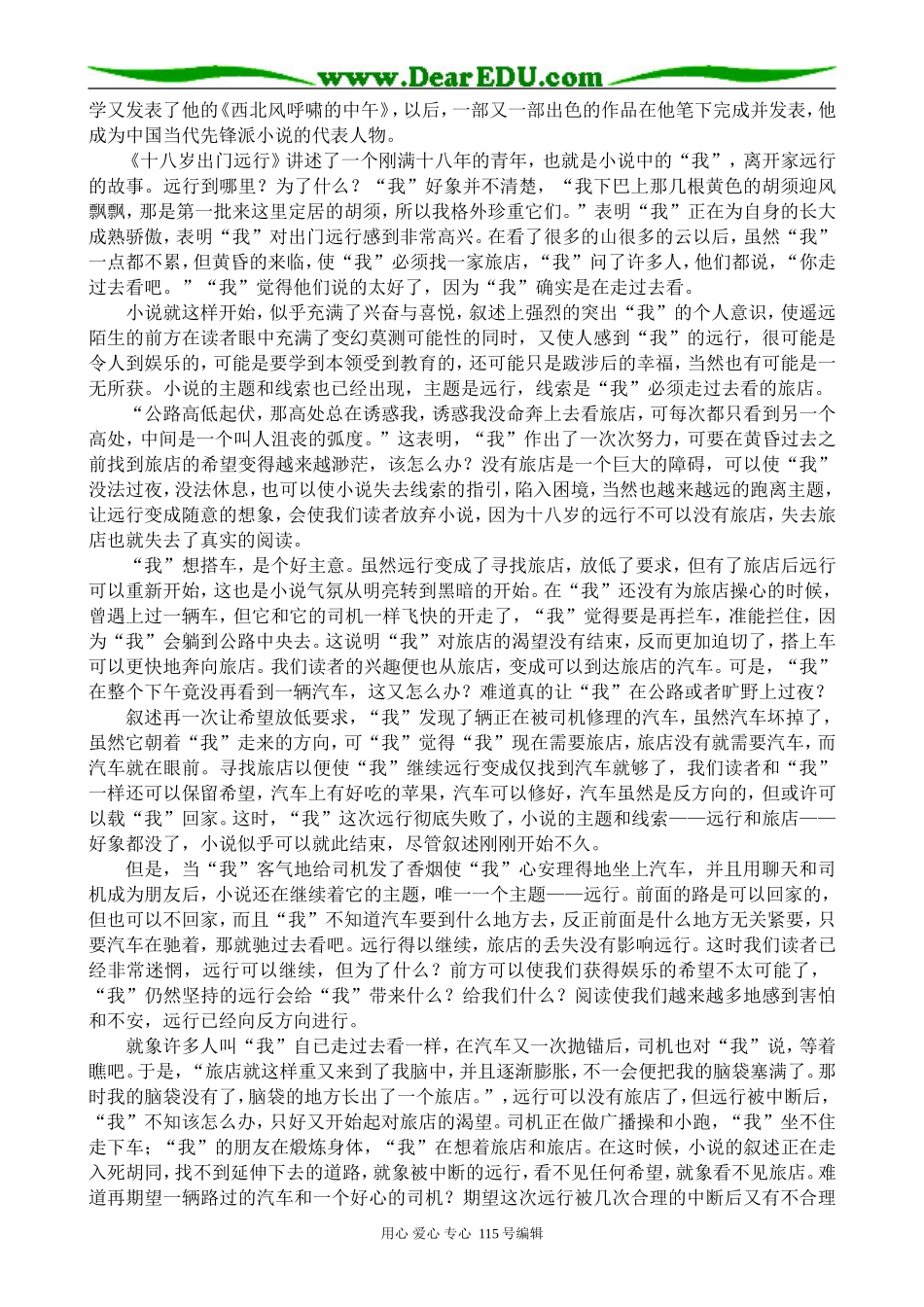十八岁出门远行【背景资料】一、作者简介《十八岁出门远行》作者余华,1960年生,浙江海盐人。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等几十个短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偶然事件》和长篇小说《在烟雨中呼喊》、《活着》等,为近年十分活跃的新潮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余华的小说从其叙述风格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但又不同于传统故事小说。另一类则借鉴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搅乱时空界限,制造神秘氛围还原欲望骚动,表现心理变态以及意识混乱的种种奇异感觉。但无论注重写实还是侧重还原感觉,余华都对人性中黑暗、丑恶、残忍的一面进行无情的暴露。他写不可知的预感,写令人不寒而栗的死亡场面,写扭曲、乖戾、怪诞的人性……这一切再加上那无动于衷的冷漠的叙事态度,可以说,余华把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的冷漠之潮推到了冷酷的深处。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的确,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开头的一段描写,表现迷蒙离奇、漂浮不定的感觉,令人宛若是在梦中。而小说愈发展则梦的成分就愈强:汽车突然的出现,后来又突然的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司机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视若不见,还对着“我”快意地大笑不止。整个过程犹如发生在梦境里一般,充满了怪诞和不可思议。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它用多种可能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让人感受到一种由悖廖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余华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恰切注释,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潮对作品的影响。荒诞派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说过:“荒谬就是没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余华正是用一种极而言之的“仿梦”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荒谬人生面前的深刻迷惘,而作品所剖示的“我”在青春初旅中的种种微妙的心情,则印证了存在主义大题海德格尔关于心情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被抛入世界后首先产生的是种种心情的理论,艺术地完成了对人的存在命题的揭示。小说中青春初旅的明朗欢快与荒诞人生的阴暗丑陋构成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碰撞,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审美张力。当然,《十八岁出门远行》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与悖廖无疑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作品中青春心情的起伏转变更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成长历程中心理轨迹的传神剖示。同时,纯净的语言,精巧的叙述技巧,又使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实体,而它的内在精神则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二、生活在远方——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导读(刘晓洁)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被选入高一《语文读本》中。从题目看,这篇小说似乎属于西方十八、九世纪曾盛行的成长小说类型。但作者并没有以写实的手法讲述一个青少年如何成长的故事,只是截取“远行”路途中极富隐喻的一个断面,浓缩表现了青春之旅的渴羡、期盼和迷惘的复杂心情。然而,作为接近十八岁的学生,他们不仅无法解读其中模糊不定的意象,而且对那些荒诞离奇的情节更是无从把握。如何让学生走进文本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结合学生已有的阅读经验和生活体验,从小说的情节和意象入手。(一)荒诞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人生的第一次悖谬学生过去所接触的课文,大部分都是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即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如果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解读《十八岁出门远行》,那只能是一头雾水。当然这也并非是一篇完全意用心爱心专心115号编辑义上的现代主义作品,例如文章的开头讲述“我”如何在公路上欢快地奔跑这一情节,并不晦涩,学生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抢苹果这一情节就令学生费解:我为维护司机的苹果,被人打得浑身挂彩,而司机却与打劫者扬长而去。其实,...